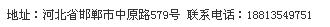诺奖作家凯尔泰斯关于奥斯维辛,电影辛
诺奖作家、奥斯维辛见证者凯尔泰斯3月31日去世,享年86岁。
有人说,他是一位哲人,
他的哲思不是来自形而上学的冥想,
而是酿生于与生俱来的磨难,
就像伤口里渗出的浓血或春野里蓬生的野花。
凯尔泰斯(.11.9-.3.31)
年,凯尔泰斯生于布达佩斯的一个犹太家庭。14岁那年夏天,他与44万名匈牙利犹太人被一同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见证了人间最惨无人道的暴行。次年他被转移到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在那里关押至被苏军解放。他曾回忆说,“当你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你没有质疑过对生活的信任。但当类似奥斯维辛的情况发生后,一切都分崩离析。”
关押在奥斯维辛的凯尔泰斯
二战后,他回到家乡布达佩斯,成为了一名记者和翻译。他翻译了尼采、弗洛伊德、维特根斯坦和埃利亚斯·卡内蒂的作品,并受加缪和萨特的战后存在主义小说的影响,他对处在极权环境下的个体命运着迷。
大屠杀是他笔下作品的永恒主题。他的处女作《命运无常(Fateless)》以第一人称叙述了一个男孩在集中营的故事。小说震动世界,令他声名鹊起,然而,这部一版再版的作品却经历了十年周折才得以在年出版。
凯尔泰斯说,《命运无常》遭受了这么久的禁忌,一方面是因为匈牙利当局和公众对大屠杀的认识仍然微不足道,尽管纳粹及其匈牙利党羽杀害了大约50万匈牙利犹太人;另一方面,也因为它反映了匈牙利的独裁制度。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关于屠杀、独裁和自由的作品层出不穷,凯尔泰斯的写作赢得了圈内的认可,但未能吸引广泛的受众。自从年以《命运无常》及其他作品赢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一切都改变了。他是匈牙利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数百人会为了他的签名而排上几个小时的队。然而,他在接受提名时的演讲中说,他只为他自己写小说,“我没有一个观众,不想影响任何人。”
青年时代的凯尔泰斯
凯尔泰斯严厉批评了史蒂芬·斯皮尔伯格的电影《辛德勒的名单》,“很显然,这个根本没有在战争时代生活过的美国人斯皮尔伯格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纳粹集中营真实的情景。可是,他又为什么要不遗余力地把一个自己并不认识的世界搬上银幕,并让人们觉得每一个细节都确实可信呢?我认为,斯皮尔伯格这部黑白电影中最有问题的地方,是在影片末尾以彩色出现的胜利的人群。电影中那些没有涉及奥斯维辛深远影响的伦理道德问题的描写,我也认为是一种拙劣,因为根据它所表现的伦理道德,作为关键性的人——及人文的理想——此时此刻竟然完好无恙地走出了奥斯维辛。倘若是这样,那么我们今天就没必要再谈论什么种族屠杀了,
凯尔泰斯时常被自杀的念头困扰,在年的小说《清算》中,他让书中的主人公以自杀而告终。
年,在与帕金森综合症战斗的最后阶段,凯尔泰斯在柏林的家中接受了《巴黎评论》的采访。他说,纳粹政权“是一台高效运转的机器,以至大多数人都没有机会了解他们所经历过的事情。”至于他的文学动机,“我试图去与一些真相缠斗,讲一个不被允许讲出来的故事。我是从这一切当中幸存下来的人。”
▍凯尔泰斯如是说
假如你的存在并非不可思议,那么就连提它都没有意义。
也许,我们之所以能够承受生活,是因为这个生活竟如此的不真实;另一方面,因为意识总在不断地窥视所谓的真实,它渴望真实。
不用去理解世界,只因为它不可理解:浅显而言,我们之所以不理解世界,是因为这不是我们活在地球上该做的事情。
我们不要过度的思考,要么变得不幸,要么变得神秘。维特根斯坦最终也变得神秘,就像卡夫卡一样。只不过他是用另一种材料思考:用逻辑。应该摧毁这个世界,直到信仰突然像晶莹的宝石一样从废墟的下面闪烁发光。此刻,我想象中的他正手里捧着宝石:端详,端详,但想不起它的名字。不过他知道:奇迹发生了,已经得救了忘记,奥斯维辛根本不是由于奥斯维辛的过去而被废除的,而是因为军事格局的转变;奥斯维辛之后,什么都没有发生,我们并未因谴责了奥斯维辛而得以生存。然而,我们却经历了那些以意识形态为治国之本的帝国;从实用角度讲,这些意识形态不仅被证明为语言游戏,甚至还使这种语言游戏得以实际应用,这种意识形态本身变成了一种具有恐怖效应的统治工具。
“就在这一刻,我仿佛站在生与死的门槛上,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理解,身体向前冲着死亡,而头却回望,朝着生活的方向,我就要迈开的腿迟疑地抬起……将要去哪儿?其实无所谓,因为,这个将要迈步前行的人已经不再是我,而是另一个人……”
现在,究竟通过“变化”发生了什么变化?难道不再受人摆布?难道我自己救赎了自己?所发生的变化只不过是他们归还了我最低限度的生存条件,我的个体自由—牢房门“吱呀”作响,但还是打开了,我在这里已被囚禁了整整四十年,可以想象,这一声“吱呀”就足以使我惶惑不安。我们不能在自己当过奴隶的地方体验自由。必须离开这里,去很远的地方。但我做不到。因此,我必须为自己重新诞生,变形—究竟要变成谁?要变成什么?
我们不要忘记,奥斯维辛根本不是由于奥斯维辛的过去而被废除的,而是因为军事格局的转变;奥斯维辛之后,什么都没有发生,我们并未因谴责了奥斯维辛而得以生存。然而,我们却经历了那些以意识形态为治国之本的帝国;从实用角度讲,这些意识形态不仅被证明为语言游戏,甚至还使这种语言游戏得以实际应用,这种意识形态本身变成了一种具有恐怖效应的统治工具。
——小说《另一个人:变形者札记》
只管往前走,永远别回头,死亡就在前面,看哪,你是自由的。
我们对自己活着到底能够肯定多少?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给出一个这样的回答:多少要比我们对自己死亡的肯定少一些。
分析既不能补偿,也不能代替任何过程。
在人的生命力,最终会有一个瞬间降临——就在这一刻,我们突然意识到了自己,突然释放出自己的能量;就从这一刻起,我们可以依靠自己,而且就在这一刻诞生。每个人都体内都拥有天才的幼芽,但是并非每个人都能是生活成为自己的生活。
人们询问一位隐居的年轻贵族,问他为什么不享乐生活?这个问题使贵族吃了一惊,问:“什么是生活?”“生活就是社交、竞争、朋友、娶妻、置家。”大家告诉他。“原来是这样,”贵族回答说,“假若这就是生活的话,那么,我的南浦男仆就可以代我处理了。”
没有比人们爱我们更令人窘促不安的感觉了。只有在冷静、客观的关系中,才有可能感到一点点真实与一点点愉悦。就连性爱,也只在远离之后才能享受;一个不知姓名的情人的肉体,转眼就会变成陌生,不再想占有的时候,根本就不渴望占有。
我们活着,是暂时的。从被人忽略了瑕疵到被人忽略了的道德事件,想一想我们的躯体,我们的灵魂和我们的生存环境,毫不在乎地挥挥手,迄今为止都还不错,就这样下去吧。在这个无可救药,没有精神升华的世界里,所有的一切都向悲剧演变,而所有的悲剧都向灾难转化。如果没能看到这一点,那很遗憾。
在早些的时代里,杀人往往并不是件恶劣的习俗,并非像犯罪那样的坏事。而是一种生存方式,一种针对生命、针对其他生灵的,已经养成了的,实用的自然行为。杀人,作为一种生存观,作为一种杀人的行为方式,毫无疑问是一种本质的变化。尽管可以这样讲,人类对屠杀的发明,并不是什么新的发明。但是,人类的屠杀经过几年,几十年持续不断地进行,已经联通与之共存的所谓正常的日常生活,儿童教育、恋爱的散步、医疗诊所的时光、事业,连同某些欲望、幸福与不幸感、文明的好奇、黄昏的忧郁、致富、失败或成功等一起,连同习惯、对恐惧的适应、默认、漠视、甚至厌恶一起,变成了一个人类的屠杀体系。
它们体内携有个体死亡的恐惧,所以才会竭力存活。所有的这些问题不过是为了使人明白,所有有意义的问题都朝没有意义引导,这种意义从来不可能导向真理,不可能导向上帝能够抵创造生灵,并使之存活的真理。即使这是真理,也不是整个的真理,而完全是其他的什么,不只是我们的语言,我们的概念,自我的直觉揣测,但是,至少在我们还是这个世界一部分的时候,或者说,至少在我们还活着的时候,根本就不存在任何种类任何样式的我们的感觉。
就我生存的自然物态而言,也跟我的意识一样陌生,我的出生也跟我的灵魂,跟我的纯粹人的生存一样陌生。
我从来未曾相信过有关这个年代的其他东西。现在我才意识到,人们始终相信着什么,并且以此度过他们所活过的人生。或者说,他们至少不相信自己度过的是自己所活过的人生。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正是这个给了他们幸存的可能,甚至给了他们幸福的生活,有时在生活中还体验到胜利的感觉。然而应该看到的是,人们于此同时也因此得了残疾。这种残疾就像是癌症,就像是巩膜炎,它如此这般地使人体钙化,并向创造力侵袭滋长。
——小说《船夫日记》
可以想见,随着鲜活感知的消退,那些难以想象的剧痛和悲哀会作为一种价值的体现继续存活在人的身上,因而不仅要坚持这种剧痛和悲哀的准确性,而且需要将其作为被普遍承认和接受的价值。
这样就形成了一种种族屠杀遵奉主义、一种种族屠杀感伤主义、一种种族屠杀的教规、一种种族屠杀的清规戒律及其仪式的语言世界,同时还形成了为种族屠杀消费而生产的种族屠杀产品,形成了对奥斯维辛的否定,诞生了欺骗奥斯维辛的人物。
我知道当我把斯皮尔伯格的电影《辛德勒的名单》称为一种拙劣时,有很多人不同意我的观点。人们认为,斯皮尔伯格为他的电影付出了大量的工作,他的电影吸引了数以百万的观众,甚至包括那些对种族屠杀这个话题不感兴趣的人。这确实是可能的。但是,作为种族屠杀的幸存者、作为依然保留着恐怖感知的人,他们有什么理由高兴让更多人在银幕上看到这种——更毋庸说是伪造的——经历呢?
很显然,这个根本没有在战争时代生活过的美国人斯皮尔伯格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纳粹集中营真实的情景。可是,他又为什么要不遗余力地把一个自己并不认识的世界搬上银幕,并让人们觉得每一个细节都确实可信呢?我认为,斯皮尔伯格这部黑白电影中最有问题的地方,是在影片末尾以彩色出现的胜利的人群。电影中那些没有涉及奥斯维辛深远影响的伦理道德问题的描写,我也认为是一种拙劣,因为根据它所表现的伦理道德,作为关键性的人——及人文的理想——此时此刻竟然完好无恙地走出了奥斯维辛。倘若是这样,那么我们今天就没必要再谈论什么种族屠杀了,或者至多当成是一个遥远历史的记忆。
把奥斯维辛只局限在直接受害者的范围内,而不将其视为世界的一个客观存在,因而把奥斯维辛降低为单单是德国人与犹太人之间的问题,降低为两个群体间某种宿命的不相容性。我当然要把这所有拙劣的东西称作是——拙劣。
——讲演《谁的奥斯维辛?》
北京白斑病医院白颠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