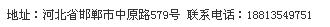伤寒卒病论6
方中生姜解表散风寒,调理卫气,走里散水气。芍药和营,与生姜相用,和营之中以调和卫气。白术健脾燥湿,使水有所制所行。茯苓健脾渗湿,使水邪有泄路,而不得内居,与生姜、白术相合,健脾制水行水。甘草、大枣益气,既助生姜、芍药以调和营卫,又协白术、茯苓健脾之中以补脾,使中气健而水邪去,并调和诸药。诸药相伍,以奏其功效。
结合临床实际,本方以不去桂枝为妥,因桂枝既有解外之功,又有助阳气化水气。徜若表邪较轻,用桂枝有致汗出多者,则当去之或少量用之。权衡去桂枝之利弊,当以具体病情而决定为是。
随证加减用药:若腹胀者,加厚朴、枳实;若胃腕支结者,加半夏、陈皮;若食少者,加莱菔子、生麦芽,等。
《注解伤寒论》:“与桂枝汤以解外,加茯苓、白术利小便行留饮也。”
《伤寒论条辨》:“去桂枝用芍药甘草者,收重阳之阴而益里伤之虚也。姜枣健胃而和中,下后用之更宜。故二物乃其阳也。茯苓淡渗以利窍。术能土以胜水,本其有停饮之故,所以加之。”
本方具有运脾利水、调和营卫作用,主治水气内停营卫不和证,可以治疗消化系统之慢性胃肠炎及溃疡、幽门水肿等;泌尿系统之膀胱炎、慢性肾炎等病证而见上述证机者。
本方具有镇痛、解热、发汗、利尿等作用。
1.2太阳伤寒证与胃寒证相兼
太阳与阳明合病,不下利,但呕者,葛根加半夏汤主之。(33)
本条辨证精神有二,其一,辨表里兼证的证候特
征;其二,论病当表里同治。辨表里兼证,从仲景用方主治病证分析,则知在表是太阳伤寒证,在里则有阳明大肠和阳明胃之别,文中言“不下利,但呕者,”以揭病是阳明胃寒证,其证机是寒邪在阳明胃,并扰乱胃气而上逆。从表里病证孰轻孰重分析,表里兼证都比较明显,故其治当表里双解,以葛根加半夏汤,解表和胃。
《注解伤寒论》:“邪气外甚,阳不主里,里气不和,气下而不上者,但下利而不呕;里气上逆而不下者,但呕而不下利,与葛根汤以散其邪,加半夏以下逆气。”
解表散邪,和胃降逆。
葛根加半夏汤
葛根四两(12g)麻黄去节,三两(9g)甘草炙,二两(6g)芍药二两(6g)枝去皮,二两(6g)生姜切,二两(6g)半夏洗,半升(12g)大枣擘,十二枚
上八味,以水一斗,先煮葛根、麻黄,减二升,去白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覆取微似汗。
方中麻黄辛温,解表散风寒。葛根鼓舞胃气而升津,布达津液而濡筋。桂枝解肌散邪,与麻黄相合,以增强宣卫开营,与葛根相合,以增和中升津舒筋。半夏长于温中降浊理气机,并能散胃中寒邪,与桂技相合,温暖中气,散寒降逆;与葛根相合.以使中焦清者升,浊者降。生姜辛温解表,温胃散寒,与麻黄、桂枝相合,以增强解表发汗;与半夏相合,以达调理中气而散寒。芍药益营,与麻黄、桂枝相合,使营气和协于卫,以达营卫和合而发散风寒;与生姜、半夏相用,以达散寒降逆之中兼制辛燥耗胃阴,并有缓急和中,尤其与甘草相合,则和中解外更为突出。甘草、大枣补益中气,与半夏相用,散寒之中以补中益气,又益汗源,使桂枝、麻黄有汗可发,表邪尽从汗出,更能调和诸药而显其效用。
随证加减用药:若呕吐明显者,加陈皮、吴茱萸;若大便溏者,加自术、茯苓,等。
《绛雪园古方选注》:“葛根汤,升剂也。半夏辛滑,芍药收阴,降药也。太阳、阳明两经,开失机,故以升降法治之。麻、葛、姜、桂,其性皆升,惟其升极即有降,理寓其中也。又有芍药、甘草奠安其中焦,再加半夏以通阴阳,而气遂下呕亦止,是先升后降之剂也。”
本方具有解表散邪、和胃降逆作用,主治脾胃不和、卫闭营郁证,可以治疗急性肠胃炎、慢性非特异性疡性结肠炎以及肠胃型感冒等病证而见上述证机者。
1.3太阳病证与胂胃虚滞证相兼
发汗后,腹胀满者,厚朴生姜半夏甘草人参汤主之。(66)
本条辨证精神有二,其一,辨表里兼证;其二,论脾胃气虚气滞寒证的证治。辨表里兼证,从仲景言“发汗后”以揭病以表证为主,治当先表。文中以治表未能恰到好处为借鉴,以此阐明病变的主要矛盾方面在里。病是脾胃气虚气滞寒证如“腹胀满”,时轻时重,因寒而加,因按而减。其证机是脾气虚而不运,脾气滞而不行,治以厚朴生姜半夏甘草人参汤。里证得解,若表证仍在者,再以法治其表。
《伤寒贯珠集》:“发汗后,表邪虽解,而腹胀满者,汗多伤阳,气窒不行也。是不可以徒补,补之则气愈窒,亦不可以迳攻,女之则阳益伤,故以人参甘草生姜助阳气,厚朴半夏行滞气,乃补泄兼行之法也。”
温运牌气,行气除满。
厚朴生姜半夏甘草人参汤
厚朴炙,去皮,半斤(24g)生姜切,半斤(24g)半夏洗,半升(12g)甘草炙,二两(6g)人参一两(3g)
上五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
方中厚朴苦温,苦以下气除滞,温以行气消满使脾胃气机得以畅通。生姜辛温,辛以宣散滞气.温以和胃降逆消
食,与厚朴相伍,降胃气,运脾气。半夏辛温,辛以醒脾气之滞,温以降浊开结行滞,与厚朴、生姜相伍,以增行气除满。人参温补脾胃,使脾胃主运主纳。甘草补中,与厚朴、生姜、半夏相伍,使其行气除满不伤中气;与人参相伍,补脾胃,益中气,除胀满,并调和诸药。诸药相伍,补而不滞,消而不伤,以疗脾胃气虚气滞寒证。
随证加减用药:若少气者,加黄芪、白术;若腹痛者,加芍药、木香;若便溏者,加茯苓、山药;若脾湿者,加薏苡仁、扁豆,等。
《注解伤寒论》:“厚朴之苦,以泄腹满。人参、甘草之甘,以益脾胃。半夏、生姜之辛,以散滞气。”《金镜内台方议》:“故用厚朴之苦,以泄腹满为君。生姜、半夏之辛,以散滞气为臣。人参之甘,生津液,补不足。甘草之甘,以缓其中者也。”
本方具有温运脾气、行气除满作用,主治脾胃气虚气滞有寒证,可以治疗慢性胃炎、慢性肝炎、慢性肠炎、慢性胆囊炎、慢性胰腺炎等病证而见上述证机者。
1.4太阳病证与脾胃寒证相兼
病人有寒,复发汗,胃中冷,必吐蛔。(89)
本条辨证精神有二,其一,辨表里兼证;其二辨脾胃寒证的审证要点。辨表里兼证,从仲景言:“复发汗,胃中冷。”以揭表里兼证,文中先言“复发汗”,以揭病以表证为主,治当先表。但在治表时一定要谨守证机,方可应期愈疾。
本条辨表里兼证,由于脾胃素体有寒,即使病以表证为主,其治当先从表,但也要做到治表不伤脾胃或权衡治法时尽可能照顾到脾胃。如果仅仅治表而失里,不仅达不到治疗目的,反而还会加重脾胃病证,如呕吐等,若素体有蛔则蛔可因呕吐而出。
《伤账论译释》:“病人有寒,指平素阳气不足,中
焦虚寒,虽有表证,亦不可发汗,只能温中助阳以和肌表,如径用一般的发汗方法,必致阳气外越,中阳更虛,里寒更甚,而发生吐逆。如果肠道有蛔虫寄生,则蛔虫不安而上行,可随呕吐而出
1.5太阳伤寒证与阳明胃热盛证相兼
伤寒,脉浮,发热,无汗,其表不解,不可与白虎汤;渴欲饮水,无表证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17)
本条辨证精神有三,其一,辨表里兼证;其二辨白虎汤治疗禁忌;其三,辨阳明热盛津气两伤证的证治。辩表里兼证,在表当是太阳伤寒证,在里当是阳明胃热盛证。病为表里,里热虽盛,但以表证为主,治当先表,表解之后,方可治其里,以白虎汤。正如文中所言:“其表不解,不可与白虎汤。
表里兼证,论治有先后之序,若其治稍有不当,因用解表发汗而伤津气,以此而加重阳明胃热证,同时又出现汗后伤津伤气,而演变为阳明胃热津气两伤证,其治当清泻胃热,益气生津,以白虎加人参汤。
本条从辨表里兼证入手,从辨阳明胃热证为笔法,以治法未能恰到好处为借鉴,进而把辨证的重点放在辨阳明胃热津气两伤证上,并以此展开辨证论治。
《伤寒六经辨证治法》:“此有表,戒白虎汤也。脉浮发热无汗,为寒邪在表,白虎则不可与,因白虎汤但能解热,而不能解表,务必恶寒,头疼,身痛表证尽除,阳明邪炽,惟有热渴求救于水者,方可与之。
清泻盛热。
白虎汤
知母六两(18g)石膏碎,一斤(48g)甘草炙,二两(6g)使米六合(18g)
上四味,以水一斗,煮米熟,汤成,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
方中知母苦寒,善于清阳明胃热,生津以除烦止渴。石膏辛甘寒,寒与知母相合,以增泻热,甘与知母相用,以增生津养阴退热,辛与知母相合,善使里热既从内消又从外泄。粳米、甘草补中益气而生津,使津复以退热,并制约知母、石膏苦寒伤气,使知母、石膏泻热而不寒凝,更能调和诸药。诸药相合,共奏消泻盛热之效。
随证加减用药:若心烦者,竹叶、栀子;若口渴者,加天花粉、芦根、生地;若热毒盛者,加连翘、银花,等。
《伤寒内科论》:“方中知母苦寒,善清阳明胃热。石膏辛甘寒,善使里热透达于外。甘草、粳米一面补中益气而生津,一面制苦寒之品伤胃气。诸药相使,共奏清泻阳明盛热之功。”
吴琨《医方考》:“石膏大寒,用之以清胃。知母味厚,用之以生津。大寒之性行,恐伤胃气,故用甘草、粳米以养胃。
本方具有清泻盛热作用,主治邪热内盛证,可以治疗流行性脑脊髓膜炎、乙型脑炎、脑卒中、流行性出血热、钩端蝶旋体病、大叶性肺炎、疱疹性口腔炎、顽固性过敏性皮炎、甲状腺机能亢进症、糖尿病、青光眼、巩膜炎、急性肠胃炎、败血症等病证而见上述证机者。
白虎汤具有对伤寒、副伤寒菌苗所致家免发热有一定解热作用);对内毒素所致家兔发热有退热作用);有解热作用,抗炎作用,降低血糖作用,抑菌作用,镇静镇痛作用,抗惊厥作用等。
清泻盛热,益气生津。
白虎加人参汤
知母六两(18g)石膏碎,绵裹,一斤(48g)甘草炙,二两(6g)粳米六合(18g)人参三两(9g)
上五味,以水一斗,煮米熟,汤成,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此方立夏后,立秋前乃可服,立秋后不可服,正月二月三月尚凛冷,亦不可与服之,与之则呕利而腹痛。诸亡血,虚家,亦不可与,得之则腹痛利者,但可温之,当愈。
方中知母苦寒,善于清阳明胃热,生津以除烦止渴。石膏辛甘寒,寒与知母相合以增泻热,甘与知母相合以增生津养阴送热,辛与知母相合,善使里热既从内消又从外泄。人参益气而生津。粳米、甘草补中益气而生津,与人参相伍,以治气阴两伤,以使津复以退热,并制约知母、石膏苦寒伤气,使知母、石膏泻热而不寒凝,更能调和诸药。诸药相合,共奏清泻盛热,益气生津之效。
白虎加人参汤有其主治证,也有其禁忌证,若非热证则不当服之,服之则寒气内乘而相结,寒气与浊气相结而上逆则呕;寒气与清气相搏而下趋则利:气机为寒气所凝而不通则腹痛。文中同时又指出寒气所致腹痛下利证,其治当用温阳散寒,寒气得散得温,则腹痛呕利证自除。随证加减用药:若津亏者,加麦冬、生地;若气伤明显者,加黄芪、白术;若阴血不足者,加熟地、龟版;若汗出多者,加五味子、牡蛎、等。
《绛雪园古方选注》:“石膏辛寒,仅能散表热。知母苦寒,仅能降里热。甘草、粳米仅能载药留于中焦。若胃经热久伤气,气虚不能生津者,必须人参养正回津,而后白虎汤乃能清化除燥。
本方具有清泻盛热、益气生津作用,主治热盛津气两伤证,可以治疗甲状腺机能亢进症、糖尿病、再生障碍性贫
血、急性食道炎、急性胃炎、痢疾、日射病、热射病、成人特应性皮炎发热、口渴、大叶性肺炎、乙型脑炎、流行性脑炎等病证而见上述证机者。
白虎加人参汤具有降低血糖作用,解热作用,提高机体免疫机能的作用,协同抗癌药抗癌作用,抗过敏作用等。
1.6太阳伤证与胃热津气两伤证相兼
伤寒,无大热,口燥渴,心烦,背微恶寒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
本条辨表里兼证。言“伤寒”以揭在表为太阳伤寒证,审里证为阳明胃热津气两伤证。审度表里兼证,辨表证而不言病证表现,从其病证表现分析,则知本条重在辨阳明胃热津气两伤证,其病证表现是:“伤寒,无大热,口燥渴,心烦,背微恶寒者。”其证机是邪热不仅消灼阴津,而且也耗伤正气,卫气因之而不能固护肌表。审病是胃热津气两伤证,其治当先里,用白虎加人参汤,清热益气生津。
本条从辨表里兼证入手,从辨阳明胃热津气两伤证为重点,同时还暗示辨阳明胃热津气两伤证之背微恶寒有类似太阳病证,当注重鉴别诊断。
《注解伤寒论》:“无大热者,为身无大热也。口燥渴,心烦者,当作阳明病,然以背微恶寒为表未全罢,所以属太阳也。背为阳,背恶寒,口中和者,少阴病也,当与附子汤。今口燥而渴,背虽恶寒,此里证也。则恶寒亦不至甚,故云微恶寒,与白虎汤和表散热,加人参止渴生津。”
7太阳中风证与肾热津气两伤证相兼
服挂枝汤,大汗出后,大烦渴不解,脉洪大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26)
本条辨表里兼证,在表为太阳中风证,在里为阳明胃热气津两伤证。从仲景所言“大汗出后”暗示两方面的辨证内
容,一是指表里兼证,以表证为主,治当先表;二是指用桂枝汤解表,未能遵守当汗出而不当大汗出,大汗出则易诱发或加重里之病证。
本论表里兼证经发汗治表之后,病变的主要矛盾方面已发生转化,即阳明胃热津气两伤证,其审证要点是:“大烦渴不解,脉洪大者。”其证机是阳明胃热,消灼津液,涌动血脉。治当清热生津益气,以白虎加人参汤。
条与26条在里同论阳明胃热津气两伤证。在表一是太阳伤寒证,一是太阳中风证,但其病变主要矛盾方面都是在里,故其病理演变均因素体而为胃热津气两伤证。其在里证机相同,故治均以白虎加人参汤。若里证得解,表证仍在者,再以法治其表。
《伤寒内科论》:“本条论外有太阳病,内有胃中蕴热证。夫病有蕴热,复加外感,表里兼证,揣测证机,当先解其外,外解已,方可疗其里。但里有蕴热,外有表证,以挂枝汤,必当谨守用法:“遍身絷絷微似有汗者益佳,不可令如水流漓,病必不除。此因大汗出后,或表邪从汗而解,或表邪乘汗后伤津而传入于胃,以加重里疾,呈阳明胃热盛证。”
1.8太阳中风证与脾胃虚寒证相兼
太阳病,外证未除,而数下之,遂协热而利,利下不止,心下痞硬,表里不解者,桂枝人参汤主之。()
本条论表里兼证的证治。辨太阳病,而仲景特言“外证未除”",以揭病以表证为主,治当先表,使表邪从外而散,但仲景同时又指出,因辨证未能恰到好处,误认为病以里证为主,进而又指出辨证未能切中证机,以法选用针对证机的方药,以此而又多次误用下法治疗脾胃虚寒证,势必加重脾胃病证。于此伸景特言“而数下之”,以提示辨脾胃虚寒证有类似可下证,当注重鉴别诊断。
本文以一误再误的笔法,借以说明误用下法,势必加重里之病
证。对此仲景以治法不当为借鉴,将辨证重点转移到以辨里证为主。审里是脾胃虚寒证,其病证表现是:“遂协热而利,利下不止心下痞硬,表里不解者。”其证机是脾胃虚寒,寒气凝结,气机不通,浊气壅滞,太阳受风寒而呈卫强营弱。治当温中散寒,兼以解表,以桂枝人参汤。
《伤寒论后条辨》:“太阳病外证未除而数下之,表热不去而里虚作利,是曰协热。利下不止,心下痞硬者,里气虚而土来心下也,表里不解者,阳因痞而被格于外也。桂枝行阳以解外,理中助阳于内以止利,阴阳两治,总是补正令邪自却”
温补中气,解肌散邪。
桂枝人参汤
桂技别切,四两(12g)甘草炙,四两(28g)白术三两(9g)人参三两(9g)干姜三两(9g)
上五味,以水九升,先煮四味,取五升,内桂,更煮取三升,去淳。温服升,日再夜一服
方中桂枝量大,走于肌肤营卫则解肌散风寒,入于脾胃则温中散寒和阳气。人参补益牌胃之气,寓扶正以驱邪,与桂枝相合,则补阳又补气,补而不腻,并通调气机;与干姜相合,补气又温阳,温阳以散寒,散寒以和脾胃,使中气立面寒邪去;与白术相合,补脾胃又健脾胃,使脾胃虚弱之气得补;与甘草相合补益之中有调和。干姜温中散寒,与白术相合则散寒健脾,重在健中气以御寒袭或不致寒邪内生;与甘草相合则补气又散寒。甘草又调和诸药,诸药相合,以奏其功。
随证加减用药:若腹胀者,加厚朴、陈皮:若腹中寒冷者,加附子、细辛;若呕吐者,加半夏、生姜;若大便溏者,加茯苓、山药,等。
《伤寒内科论》:“本方即由理中汤加桂枝而成,桂枝走太阳解肌以散邪,走太阴阳明温脾胃而通阳,并助理中汤温中散寒止利降逆以转升降之机。诸药相合,温里为主,解肌为次。在
临床中应用该方有里而无表者,亦相宜。”
本方具有温补中气、解肌散邪作用,主治脾胃虚寒卫强营弱证,可以治疗体虚型感冒以及慢性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及十二指肠溃疡、慢性肝炎、慢性胰腺炎、慢性结肠炎等病证而见上述证机者。
19太阳温病证与阳明胃热证相兼
太阳病二日,反躁,凡熨其背而大汗出,大热入胃,胃中水竭,躁烦,必发谵语,十余日振栗,自下利者,此为欲解也。故其汗从腰以下不得汗,欲小便不得,反呕,欲失溲,足下恶风,大便硬,小便当数,而反不数及不多,大便已,头卓然而痛,其人足心必热,谷气下流故也。()
本条辨表里兼证。表为太阳温病证,从仲景言大热入胃”之“大热”以证之;里为阳明胃热证,从仲景言“大热入胃”之“入胃”证之。病以太阳病证为主,治当先从太阳,但治太阳若未能以法而治,则会引起大汗出不解或变生他证。审太阳病病邪之所以传入阳明胃,除了治疗不当因素外,决定的条件是素体胃有失调。若阳明胃素体没有失调,则太阳病病邪不一定传入于阳明胃,邪传因素体失调而异。
本条从辨表里兼证入手,以治太阳病不如法为借鉴,进而阐明辨阳明胃热证上,并以此将辨阳明胃热证的辨证思路展开。
辨阳明胃热证的病理变化及其转归,其辨证精神有三。其一阳明胃热证,如“躁烦,必发谵语。”其证机是胃中大热,邪热內灼外攻而上扰神明,可其在某种情况下,因机体阴阳自我恢复.其在病愈之前则呈现“振栗,自下利”,此因正气与邪气相争,邪气不胜正气,病邪可从下利而去,病可自我向愈。但应注意,在正气蓄积力量奋起抗邪之前,邪气相对处于优势,则会出现病证加重一旦正气充沛,病证因邪不胜正而消退。
其二,阳明胃热证在某种情况下,其病愈之前则呈现“头卓然而痛”,其证机是浊气欲泄而乘机以猖獗,阳气欲和欲通而一时乍虚于上,这是病证向愈之佳象。
其三,论阳明胃热证可能会出现一些错综复杂的病情,如“故其汗从腰以下不得汗,欲小便不得,反呕,欲失溲,足下恶风,大便硬,小便当数,而反不数及不多。”其证机是阳明胃热,热灼阴津而外攻,津为热伤而不能托邪于外,胃中浊气内壅而上逆。对此必须仔细辨证,抓住证机所在,以法论治。
文中最后指出,阳明胃热证,其病为向愈的病理机转及其特征,即“头卓然而痛,其人足心必热,谷气下流故也。”辨“头卓然而痛”,其证机是阳明胃热,阳气郁于头,阳明胃热得解,阳气周流于全身,头中阳明一时乍虚所致。
《伤寒论后条辨》:“太阳病二日,邪方在表,不当发躁,而反躁者,热气行于里,为病温之类也。反熨其背以取汗助阳夺明,阴液外亡,遂大汗出,邪未外解,而火热已人胃矣,汗既外越,火复内攻,胃汁尽夺,是为胃中水竭,水竭则必躁烦,躁烦必谵语,皆为火热入胃,火无水制之故也。十余日,则正气渐复,忽焉振栗者,邪正争也,自下利者,正胜而邪不能容,火热从大肠下夺也,火邪势微津液得复,此为欲解之象
1.10太阳病与脾热痞证相兼
伤寒大下后,复发汗,心下痞,恶寒者,表未解也;不可攻痞,当先解表,表解乃可攻痞;解表宜桂枝汤,攻痞宜大黄连泻心汤。()
本杀辨表里兼证文中从仲景先言“大下后”,以揭表里兼证以里证为主,治当先里,然后当“发汗”。仲景以用下用汗之后,以揭示表里兼证虽经治疗,但都未能切中证机,其表里病证仍在,可病变的主要矛盾方面则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里证为主而变为表证为主,此治则当随之而变,且不可固守原之病证而治之。
辨表里兼证,病以表证为主,别太阳病是太阳中风证,治宜桂枝汤;审里是脾胃热痞证,治宜大黄黄连泻心汤。
本条辨证还暗示,用“大下”的方法治疗脾冒热痞证,是不能达到预期治疗目的,治疗脾胃热痞证的最好方法是用大黄黄连泻心汤。
本条辨证是从动态中辨证,揭示病证表现的复杂性和变化性,提示治疗不能固守原法,必须因病证变化而重新确立治疗方法,以期方药与证机相应。
《伤寒贯珠集》:“大下复汗,正虚邪人,心下则痞,当与泻心汤如上法矣。若其入恶寒者,邪虽人里,而表犹未罢,则不可迳攻其痞,当先以挂枝汤解其表,而后以大黄黄连泻心汤攻其痞。不然,恐痞虽解,而表邪复人里为患也,况痞亦必能解耶。
泄热,消痞,和胃。
大黄黄连泻心汤
大黄二两(6g)黄连一两(3g)上二味,以麻沸汤二升,溃之,须臾,绞去降。分温再服。
大黄苦寒,泄热和胃而通畅气机。黄连苦寒,清泄胃中邪热以和中焦升降气机,与大黄相伍,使热去气畅,滞通痞消。又因大黄、黄连苦寒气厚味重,煮之后,多走肠胃而具泻下作用,故本方用法不取煎煮而用滚开的沸水即麻沸汤浸泡,少顷绞汁即饮,以取其气,薄其味,旨在清泄中焦无形之热,而不在泻有形之物,此乃煎煮之妙也。
《伤寒溯源集》:“故用大黄之苦寒泄之,以攻胃分之邪热。黄连之苦寒开之,以除中焦之郁热,而成倾痞之功,在五等泻心汤中,独为攻热之剂。”
《伤寒论辨证广注》:“故用沸汤,渍绞大黄黄连之汁温服,取物之与此为邪热稍轻之
证,大抵非虚热也。
本方具有泄热、消痞、和胃作用,主治脾胃热郁证,可以治疔循环系统之高血脂症、血管硬化、脑血栓形成等;消化系统之上消化道出血、急慢性肠胃炎、HP相关性胃病等;呼吸系统之肺结核出血、支气管扩张咯血等;精神、神经系统之精神分裂症、三又神经痛等;五官科之急性溃疡性口腔炎、小儿急性口疮、牙齦炎、以及慢性骨髓炎、乙型脑炎、急性扁桃体炎等病证而见上述证机者。
1.11太阳病证与脾胃虚寒证相兼
发汗后,水药不得入口为逆;若更发汗,必吐下不止。(76)
本条辨表里兼证。从文中言治到治后出现的病证分析,则知仲景辨证精神有二。其,辨表里兼证,病以表证为主,治当先表,但治表不仅未能切中证机,反而又损伤脾胃阳气,以此而加重里证。对此如果继续再用汗法治疗,则会大伤脾胃之阳而变生诸证。正如文中所言“必吐下不止。”
其二,辨表里兼证,假如病以里证为主,且因辨证失误,以先用汗法,用汗法治疗之后,则会更加损伤脾胃之气,由此而变生上吐下泻证。
本条辨证重点不是辨表里兼证,而是以论表里兼证为笔法,以治法不当为借鉴,重点论述脾胃虚寒证的病证表现是“吐下不止。其证机是脾气大伤而清气下陷,胃气大伤而浊气上逆。其治当温脾暖胃,升清降浊。
本条暗示辨证要准确,论治要恰当,力争做到用方与证机切切相应,以期达到愈疾之目的。
《伤寒论浅注》:“发大汗之后,水药不得入口,以汗本于阳明水谷之气而成,今以大汗伤之,则胃气大虚,不能司纳如此,此为治之之逆。若不知而更发其汗,则胃阳虚败,中气不守,上下俱脱,必令吐下不止,此与五苓证之水逆何涉哉。”
2.以论表里兼证为借鉴,暗示杂病辨证论治
2.1脾胃痞证及辨证要点
脉浮而紧,而复下之,紧反入里,则作痞,按
之自濡,但气痞耳。()
本条辨表里兼证,以“脉浮而紧”代表有太阳病以“而复下之”代里有病证。仲景言“而复下之”,以示表里兼证病以里证为主,治里之际一定要权衡证机所在,不可多次用下,用之不当,则会引表邪内陷即“紧反入里”而加重里之病证。文中以治法不当,把辨证的重点引向辨脾胃痞证上,辨脾胃痞证,其证机是脾胃之气,当升而不升,当降而不降,清浊之气壅滞于心下。其审证要点是:“按之自濡,但气痞耳。”
《伤寒论条辨》:“濡与软同,古字通用,复亦反也。紧反入里,言寒邪转内伏也。濡,言不硬不痛,而柔软也。痞,言气隔不通而痞塞也。”
22脾胃热证的证治
心下痞,按之濡,其脉关上浮者,大黄黄连泻心汤主之。()
本条辨脾胃热痞证,不是以论辨表里兼证为笔法而论述的,而是直接从内伤杂病角度论述脾胃热痞证。
本条辨证主要揭示脾胃热痞证既是内伤杂病中极为常见的证型,也是外感病在其病变过程中证型之。结合临床,脾胃热痞证多见于内伤杂病,而少见于外感病,对此要有足够的认识。又提示辨内伤脾胃热痞证,其常见脉证是:“心下痞,按之濡,其脉关上浮者。”其证机是邪热在脾胃,脾胃清浊之气与邪热相互搏结于起而壅滞在心下。从其脉象看,很像是表里兼证,但仔细审辨脉象部位及特征,即知病是里证,而非表里兼证。审里证是脾胃热痞证,其治以大黄黄连泻心汤。
本条论内伤杂病,是仲连类而及的一种辨证方法,其目的是为了把某一类疾病的证机进一步辨清,使人们能够知此知彼,以法论治。
《伤寒溯源集》:“心下者,心之下,中院之上,胃之上脘也,胃居心之下,故曰心下也。痞者,天地不交之谓也,以
邪气痞塞于中,上下不通而名之也。…按之濡,即所谓气痞也。其脉关上浮者,浮为阳邪,浮主在上,关为中焦,寸为上焦,因邪在中焦,故关上浮也。…此则关上浮,按之濡,乃无形之邪热也。热虽无形,然非苦寒以泄之,不能去也,故以大黄黄连泻心汤主之。”
23脾胃热痛兼阳虚证的证治
心下熔,而复愚寒汗出者,附子泻心汤主之
本条不是辨表里兼证,而是辨脾胃热痞证与阳虚证相兼,病是里证相兼,其常见证候是:“心下痞,而复恶寒汗出者。”其证机是邪热在脾胃而壅滞气机,肾阳不足则不能温煦于外。但又因其在病变过程中有类似太阳病证表现,对此要注重鉴别诊断。审太阳中风证,其恶寒汗出,则有发热,而脾胃热痞兼阳虚证则无发热,以资别之。
辨里证不是单一的脾胃热痞证,而是脾胃热痞兼肾阳虚证,故其治以附子泻心汤,既清泄脾胃,又温壮阳气。
《伤寒贯珠集》:“谓心下痞,按之濡,关脉浮者当与大黄黄连泻心汤,泻心下之虚热;若其人复恶寒汗出,证兼阳虚不足者,又须加附子以复表阳之气,乃寒热并用,邪正兼治之法也。”
泄热消痞,扶阳益正。
附子泻心汤
大黄二两(6g)黄连一两(3g)黄芩一两(3g)附子炮,去皮,破,别煮取汁枚(5g)
上四味,切三味,以麻沸汤二升渍之,须臾,绞去滓,内附子汁,分温再服。
方中大黄清泄脾胃无形邪热。黄连、黄芩苦寒助大黄清泄脾胃。麻沸汤浸清,取其气清轻上扬,免其味重浊下泻以清泄中焦邪热。附子久煎别煮取汁,使辛热药物充分发挥温肾壮
阳,顾护卫气。诸药相合,寒热异其气,生熟异其性,药虽同行而功则各奏,此乃仲景组方之妙用。
随证加减用药:若口腔溃疡者,加干姜、骨碎补;若口臭者加藿香、白芷;若牙宣出血者,加生地、丹皮:若牙痛者,加升麻、细辛,等。
舒诏《舒氏伤寒集注》:“治上热下寒证,确乎有理。三黄溶浸,即经去滓,但取轻清之气,以去上焦之热。附子取浓汁以治下焦之寒,是上用凉而下用温,上行泻而下行补,泻取轻而补取重。”
《伤寒内科论》:“方中大黄、黄连、黄芩苦寒,取麻沸汤浸渍,取其气,以清泄中焦邪热。附子久煎别煮取汁,使辛热药物充分发挥温肾壮阳固表的作用。”
本方具有泄热消痞、扶阳益正作用,主治阳虚热痞证,可以治疗急、慢性胃炎、细菌性瘌疾、复发性口腔溃疡、上消化道大出血、高血压、血管神经性头痛等病证而见上述证机者。
附子泻心汤具有延长出血时间、减少血小板和白细胞计数、对体外血栓有明显抑制作用等。
24中虚湿热痞证的证治及兼论鉴别
伤寒五六日,呕而发热者,柴胡汤证具,而以它药下之,柴胡证仍在者,复与柴胡汤,此虽已下之,不为逆,必蒸蒸而振,却发热汗出而解;若心下满而硬痛者,此为结胸也,大陷胸汤主之;但满而不痛者,此为痞,柴胡不中与之,宜半夏泻心汤。()
本条辨表里兼证。在表为太阳病,里因素体失调或宿疾不同,则其里证也不尽相同,其辨则当以具体病人而定。就本条而,仲景以假设的形式论述了太阳病证兼里证的不同辨证方法及其鉴别,对辨错综复杂的病证颇有帮助。
其一,辨表里兼证,假如素体有少阳胆失调,即会出现太阳病,
证与少阳胆病证相兼。文中言“而以它药下之”,以揭表里兼证病变的主要矛盾方面在少阳。既然病证以里为主,其治当清胆热,调气机。于此仲景又指出,辨少阳胆证在某些情况下有类似可下证,对此一定要辨清证机所在,如果未能抓住证机所在而用其它方法治疗,不仅达不到治疗目的,反而还会引起其它病证。于此仲景又指出,是否引起变证,其治疗不当仅仅是一个方面,决定的条件是患者素体。假如素体尚强,虽因治法不当,也不会引起变证。如果病证仍在少阳胆,当以法而治,以小柴胡汤。仲景还明确指出经误治之后,病在向愈之际,则会出现一些特殊的病证表现如“此虽已下之,不为逆,必蒸蒸而振,却发热汗出而解。”其证机是因误下面伤正气,正气抗邪必须蓄积力量,待正气充沛而积力抗邪,正邪交争至为剧烈,然则邪不胜正蒸蒸发热,振振恶寒而邪从汗解,对此不可误为病情加重。
其二,辨表里兼证,假如素体有痰饮为患,则会引起痰饮变证。痰饮病证病机较多,临证之际仍当详细辨证。本论其审证要点是:“若心下满而硬痛者。”其证机是邪热与饮相搏,阻滞胸中气机而不通;其治以大陷胸汤,荡涤饮邪,清泄邪热。
其三,辨表里兼证,假如素体是脾胃失调或宿疾,因治不当则会出现脾胃病证。通过辨证之后,得知脾胃素体有正气虚弱,湿热内蕴,因治不当而诱发或加重脾胃病证,审证是中虚湿热痞证,其证候表现是:“但满而不痛者”,其证机是脾胃虚弱,湿热内蕴,壅滞气机,浊气不降。其治当补中泄热,除湿消痞,以半夏泻心汤。
本条辨证以假设的形式论述辨表里兼证,并以假设的形式论述表里兼证因素体不同则有不同的病证表现,又暗示治疗不当仅仅是病邪传变的一个外在条件,而决定的条件是病人的素体。因此在辨证之际,要密切注重患者素体,对提高辨证的准确率和治疗的确切性都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伤寒论译释》:“本条所述有三种情况是言误下后柴胡证仍在,因知邪未内陷,虽然误下,不是逆候,所以仍可
再用柴胡汤治疗;二是误下后邪已内陷,如果其人素有痰水,热与水结,就会发生心下满而硬痛的大结胸证,可治以大陷胸汤,三是患者素无痰水,虽然误下邪陷,仅是心下闷满,但不疼痛,这与有形邪结的结胸证不同,而是正虚邪结,胃气壅滞的痞证。邪已内陷,当然非柴胡汤所能治,而必须使用苦辛甘相伍的半夏泻心汤。
补中泄热,除湿消痞。
半夏泻心汤
半夏洗,半升(12g)黄芩三两(9g)人参三两(9g)干姜三两(9g)甘草三两(9g)黄连一两(3g)大枣擘,十二枚上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
方中黄连苦寒,苦以燥湿,寒以清热,湿热以苦寒,本为应治之机,但因湿热之邪胶结,又因苦寒易于凝滞气机,故必用半夏之辛温,辛以宣散,有利于湿热之邪溃散,温以通达,有利于气机畅通,与黄连相合,则温而不助热,寒而不凝滞气机。黄芩苦寒,助黄连清热燥湿。干姜辛温,与半夏相合,旨在调畅中焦气机,使湿热之邪因苦寒而消散。中气虚弱,用苦寒用辛温则易伤中气,因此必用人参补中益气,固本以祛邪,以恢复脾胃升降气机。大枣、甘草补益中气,助人参补中,并能调和诸药。诸药相合,辛开苦降甘调,清气得升,浊气得降,中气得复,气机得畅,诸证悉除。
随证加减用药:若胃热明显者,加栀子;若食少者,加神曲香附;若湿邪阻滞者,加苍术、川芎;若脘腹疼痛者,加元胡、川楝子,等。
《医方考》:“泻心者,泻心下之邪也。姜、夏之辛,所以散结气。芩、连之苦,所以泻痞热。已下之后,脾气必虚,人参、甘
草、大枣所以补脾之虚。”
《注解伤寒论》:“所以谓之泻心者,谓泻心下之邪也…黄连味苦寒,黄芩味苦寒,《内经》曰:苦先入心,以苦泻之。泻心者必以苦为主,是以黄连为君,黄芩为臣,以降阳而升阴也。半夏味辛温,干姜味辛热。《内经》:辛走气,辛以散之。散痞者,必以辛为助,故以半夏、干姜为佐,以分阴而行阳也。甘草味甘平,大枣味甘温,人参味甘温,阴阳不交曰痞,上下不通曰满,欲通上下交阴阳者,必和其中,所调中者,脾胃是也,脾不足者以甘补之故用人参、甘草、大枣为使,以补脾而和气,中气安和,上下得位,水升火降,则痞消热已
本方具有补中泄热、除湿消痞作用,主治中虚湿热痞证,可以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慢性浅表性胃炎、HP相关性胃炎、红斑性胃炎、胆汁反流性胃炎、胃及十二指肠溃疡、胃下垂、胃扩张、胃节律紊乱综合症、肠易激综合症、慢性肝炎、贲门痉挛、慢性胆囊炎、慢性肠炎、肿瘤化疗引起消化道反应、病毒性心肌炎、慢性肾功能衰竭以及妇科不孕证等病证面见上述证机者
半夏泻心汤具有对新斯的明引起的强烈胃运动有明显的抑制作用“;抑制蓖麻油引起的伴有炎症反应的腹泻有剂量依赖性;保护胃粘膜作用,抗胃溃疡作用,抗缺氧作用等。
2.5中虚湿热痞兼食滞水气证的证治
伤寒,汗出,解之后,胃中不和,心下痞硬干噫食臭,胁下有水气,腹中雷鸣,下利者,生姜泻心汤主之。()
本条辨表里兼证。从仲景言“汗出”以揭表里兼
证,病以表证为主,其治当先表,治表之后,则当以法治其里。审里病证,从仲景言:“胃中不和”,及其所论病证表现,如“心下痞硬,干噫食臭,胁下有水气,腹中雷鸣下利者,其证机是脾胃虚弱,湿热内结,浊气壅滞,气机不通,食而不消,水气内生。审证为中虚湿热痞兼食滞水气证,其治当补中降逆,散水消痞,以生姜泻心汤。
本条辨证从辨表里兼证入手,进而将辨证的中心引向辨内伤杂病上,以此展开辨中虚湿热痞兼食滞水气证,此辨是内伤杂病中极为常见的病证之一。
《伤寒论辨广注》:“胃不和,则脾气困而不运,以故心下痞硬。痞硬者,湿与热结也。噫,饱食息也;食臭,嗳馊酸也。……胁下有水气者,中州士虚,不能渗湿散热,以故成水而旁渗于胁下也。腹中雷鸣者,脾为阴,胃为阳,阴阳不和,因搏击有声也。夫阴阳不和,则清浊亦不分,湿热下注而为利也。故与泻心汤以开痞清湿热,兼益脾胃之气。”
补中降逆,散水消痞
生姜泻心汤
生姜切,四两(12g)甘草炙,三两(9g)人参三两(9g)干姜一两(3g)黄芩三两(9g)半夏洗,半升(12g)黄连一两(3g)大枣劈,十二枚上八味,以水一斗,煮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温服一升日服。
附子泻心汤,本云加附子、半夏泻心汤、甘草泻心汤同体别名耳。生姜泻心汤,本云理中人参黄芩汤去桂枝加黄连。并泻肝法。
方中黄连、黄芩苦寒以清热燥湿,以疗湿热之邪。半夏、干姜辛温,辛以散邪,温以畅通,使脾胃气机得以升降,使湿热之邪有泄路。人参、大枣调补脾胃之气,恢复脾胃的生理功能。生姜和脾胃,散结气,降逆气,散水气,化饮食,与半夏相用,大枣调补脾胃,并调
和诸药。诸药相合,相互为用,以建其功。
随证加减用药:若食积者,加生麦芽、菜菔子;若水气明显者,加茯苓、白术;若气逆明显者,加半夏、陈皮,等。
《伤寒来苏集》:“故用芩、连除心下之热。干姜散心下之痞。生姜、半夏去胁下之水。参、甘、大枣培腹中之虚。”
《医宗金鉴》:“名生姜泻心汤者,其义重在散水气之痞也。生姜、半夏散胁下之水气。人参、大枣补中州之土虚。干姜、甘草以温里寒。黄芩、黄连以泻痞热,备乎虚水寒热之治,胃中不和,下利之痞,焉有不愈者乎。
本方具有补中降逆、散水消痞功效,主治中虚湿热水气痞证机,可以治疗幽门梗阻、急性糜烂性胃炎,另外可参半夏泻心汤条而符合本方证机者。
2.6中虚湿热痞重证的证治
伤寒、中风,医反下之,其人下利日数十行,谷不化,腹中雷鸣,心下痞硬而满,干呕,心烦,不得
安;医见心下痞,谓病不尽,复下之,其痞益甚,此非结热,但以胃中虛,客气上逆,故使硬也,甘草泻心汤主之。()
本条辨表里兼证,从仲景言:“伤寒、中风,医反下之,”以揭辨表里兼证。在表或太阳中风证或太阳伤寒证,且病以里证为主。仲景对此以治里未能恰到好处为借鉴,以此阐明辨中虚湿热痞重证的病证表现,如:“其人下利日数十行,谷不化,腹中雷鸣,心下痞硬而满,干呕,心烦不得眠。”其证机是脾胃之气大虚,湿热内搏,清气不升而下陷,浊气内结而上逆,清浊之气又相互阻结而壅滞于心下。病至于此,文中又明确指出,辨中虚湿热痞重证,因其在病变过程中有类似邪热内结之可下证,于此一定要辨清病变的症结所在。若末能确得病本而用下法治疗,则易加重病证或致生其它变证,审证是中虚湿热痞重证.以甘草泻心汤,补虚和中,泄热消痞。
本条辨证主要揭示:其一,以辨表里兼证为笔法,将辨证的重点放在辨中虚湿热痞重证上,点明内伤杂病的辨证论治;其二,提示辨痞证,有寒热虚实之分,临证一定要仔细辨证,不得有丝毫差错,以免引起失误;其三,本条还暗示因治疗不当是否引起其它变证,其决定条件是患者素体。
文中言:“医见心下痞,谓病不尽。”主要指出医生治疗病人不能仅仅根据病者表面症状而做出治疗方案,若治疗病证未能取得预期治疗效果,病证没有完全解除,对此一定要仔细重新辨证,且不可盲目地做出治疗结论,继续复用错误的治疗方法,从而揭示辨证一定要全面审证求机,以法论治,方可免于治疗性错误。
《伤寒内科论》:“辨痞证,有实有虚,若将虚以实证而妄治之,以用下法,则致脾胃之气重虚,中焦升降斡旋之力更弱,于是致痞证不仅不除,反而更促痞证益甚。仲景有鉴于此,特曰本痞证,不仅要审辨病证表象,更为重要的是确知病机属性是虚,进而睹示辨痞证硬满,有自觉和他觉之分,自觉硬满则按之自
濡的,他觉硬满则按之如有物。本论言:‘胃中虚’,复言:“故使硬也’,提示病者自觉胃中硬满,且按之无物。言客气上逆者以示浊气不降而阻滞于上,浊气积聚而上逆也。证为中虚湿热痞重者,其治当重在补虚和中,消痞降逆,宜甘草泻心汤疗之。
补虚和中,泄热消痞。
甘草泻心汤
甘草炙,四两(12g)黄芩三两(9g)半夏洗,半夏洗半升(12g)大枣擘,十二枚黄连一两(3g)干姜三两(9g)人参三两(9g)
上七味,以水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煮三升,温服开,日三服。
按:《伤寒论》载方无人参,恐是传抄之误;《金匮要略》载方有人参,以甘草泻心汤主治病证揆度,当有人参为是。
方中甘草补中益气,和睥胃,使脾胃之气得复,能生化气血,以主持其职。黄连、黄芩清热燥湿,使脾胃不为湿热所肆虐。半夏、干姜辛温以宣畅气机,使湿热之邪因气机畅通而退却。人参、大枣补益中气,助脾胃升清降浊。甘草益气,与人参大枣相用,以增恢复脾胃之气。诸药相伍,以达苦寒泄湿热而不峻猛,辛温宣畅而不伤中气,甘补而不留恋邪气,相互为用,以建其功随证加减用药:若气虚明显者,黄芪、人参;若口腔溃疡者,加赤小豆、当归;若湿热明显者,加苦参、栀子;若胁痛者,加柴胡、元胡,等。
《绛雪园古方选注》:“故君以甘草、大枣和胃之阴。干姜、半夏启胃之阳,坐镇下焦客气,使不上逆,仍用芩、连,将已逆为痞之气轻轻泻却,而痞成泰矣。”
曹颖甫《金匮发微》:“重用解毒之甘草为君。半夏、黄连以降之。黄芩以清之。恐其败胃也,干姜以温之。人参、大枣以补之
其不用杀虫之药者,口中固无虫也。”
本方具有补虚和中、泄热消痞作用,主治中虚湿热痞以虚为主证,其治除了半夏泻心汤主治病证外,还可治疗白塞氏综合症、妇人病感染所致阴中或阴部溃疡、男子阴茎溃烂、慢性口腔溃疡、带状疱疹、口腔病毒感染等病证而见上述证机者。
甘草泻心汤具有保护胃粘膜作用,抗溃疡作用,抗病毒作用,抗炎作用,增强机体免疫机能等。
2.7中虚痰饮痞证的证治
伤寒,发汗,若吐,若下,解后,心下痞硕噫气不除者,旋复代赭汤主之。()
本条辨表里兼证。在表是太阳病,在里仲景以假设的形式论述成为可吐证或为可下证,嗜示临证时一定要辨清证机所在,以法用方。文中先言“发汗”,以暗示辨表里兼证,以表证为主,治当先表。可文中又以治表治里都未能恰到好处,以此将辨证引向辨中虚痰饮痞证上。辨中虚痰饮证,其病证表现是:“心下痞硬,噫气不除者。”其证机是脾胃虚弱,痰饮内生,阻滞气机,清浊之气壅滞于心下而逆于口咽。其治当补中降逆,化痰下气,以旋复代赭汤。
本条以辨表里兼证为借鉴,以治法不当为笔法,以治里的假设性提示辨证思路,进而将辨证的中心着落在辨中虚痰饮痞证上,并以此展开辨中虚痰饮痞证的证治要点。
《尚论篇》:“此亦伏饮为逆,但因胃气亏损,故用法以养正,而兼散微邪,大意重在噫气不除上,既心下痞硬,更加噫气不除,则胃气上逆,全不下行,有升无降,所谓弦绝者其声嘶,土败者其声哕也,故用代赭领人参下行,以镇安其逆气,微加散邪涤饮,而痞自开耳。
补中降逆,化痰下气。
旋覆代赭汤
旋覆花三两(9g)代赭石一两(3g)人参二两(6g)生
姜五两(15g)甘草炙,三两(9g)半夏洗,半升(12g)大枣,十二枚
上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
方中旋复花下气化痰散结,能升能降,升达清气,降泄浊气,疏肝利肺和中气,善疗肝气胃气上逆。代赭石重镇降逆,下气平肝和胃,与旋复花相伍,重在化痰降逆下气。人参补中益气,和肝气,善疗肝胃之气虚,与旋覆花、代赭石相伍,降逆而不降泄,补益而不助邪,化痰而不伤津。半夏燥湿化频,宣畅气机而涤饮,与人参相伍,健脾醒脾,以杜绝痰邪变生之源。生姜温胃暖肝,调和中气而化痰,与半夏相伍,重在降逆和中气。甘草、大枣补益中气,并助人参以补中,更能调和诸药。诸药相伍,补气不助逆气,化痰不伤中气,降泄而不戕伐,相互为用,以建其功。
随证加减用药:若气滞者,加紫苏、柴胡;若气逆明显者,加竹茹、柿蒂;若咽喉不利者,加桔梗、牛蒡子;若胃痛者,加元胡、川楝子,等。
《伤寒论条辨》:“旋覆、半夏,蠲饮以消痞硬。人参、甘草养正以益新虛。代赭石以镇坠其噫气。姜、枣以调和其脾胃。
《伤寒方论》:“故以人参补虚为君。代赭石之苦寒镇重而入肝领人参以下行以镇安其逆气为臣。旋覆花之成温能软坚行水下气,合姜、半开痞为佐。甘草、大枣味甘为胃之主药,故以为使。
本方具有补中降逆、化痰下气作用,主治中虚痰饮痞证,可以治疗胃及十二指肠溃疡、浅表性胃炎、胃扩张、幽门不全使阻、神经性呕吐、慢性肝炎、高底压、美尼尔氏综合症、咽神经官能证等病证面见上述证机者。
旋覆代赭汤能显著促进胃排空,促进胃动力,明显促进小肠推进,降低全血比粘度,血浆比粘度,改善微循环,促进血流等。
2.8脾胃水气痞证的证治
本以下之,故心下痞,与泻心汤,痞不解,其人渴而口燥烦,小便不利者,五苓散主之。()
本条辨证不是从辨表里兼证入手,而是直接论述脾胃水气痞证。同时指出辨脾胃水气痞证,因其在病变过程中,有些病证表现常常类似中虚湿热痞证,对此应注重鉴别诊断。文中特言“本以下之”,以据此痞证的治疗原则是利水通下,使水气为惠从下而去。若辨证失误而从中虚湿热痞证而治之,轻则无济于事重则则可加重里证。本条还明确指出,因辨证失误,治疗不当,但因患者素体而异,病证未发生他变,仍是脾胃水气痞证即“痞不解,其人渴而口燥烦,小便不利若。”其证机是脾胃中气失调,气化不及,水气内停,壅滞气机。其治当化气行水以消痞,以五苓散
《注解伤寒论》:“本因下后成痞,当与泻心汤除之。,若服之痞不解,其人渴而日燥烦,小便不利者、为水饮内畜津液不行,非热结也。与五苓散发汗散水则愈。”
2.9阳虚水气痞证
伤寒,吐下后,发汗,虚烦,脉甚微八九日,心下痞硬,胁下痛,气上冲喉咽,眩冒,经脉动惕者,久而成痿。()
本条辨表里兼证。文中先言“吐下”,后言“发汗,以示病为表里兼证,病以里证为主。并以假设的方式论述在里或为可吐证或为可下证,同时又暗示治里均末能切中证机,以此而加重里之病证,揆度里之病情,则是阳虚水气痞证,其病证表现是:“虚烦,脉甚微。”“心下痞硬,气上冲喉咽,眩冒,经脉动惕者。”其证机是脾胃阳气虚弱。水不得阳气所化而为水气,水气内停而上冲于喉咽,并走窜经脉而肆虐经气。文中仲景以用吐用下都未能切中证机为笔法,以此论治法不当,其结果不仅不能达到治疗
效果,反而还会加重病情。仲景以此论述主要在于揭示病证有类似,一定要注重鉴别诊断,不得疑似不分。
本条通过辨表里兼证,治疗通过用吐用下,进而揭示辨证一定要做到识别真伪.不能为假象所迷惑,然后指出治疗不当可引起或加重里之病证,最后把辨证的中心指向辨阳虚水气痞证上,同时指出本证如果不积极治疗,迁延失治,则会变生痿证。
《伤寒贯珠集》:“吐下复汗,津液叠伤,邪气陷人,则为虚烦,虚烦者,正不足而邪扰之,为烦心不宁也。至八九日,正气复,邪气退则愈,乃反心下痞硬,胁下痛,气上冲咽喉眩冒者,邪气抟饮,内聚而上逆也。内聚者不能四布,上逆者无以速下。夫经脉者,资血液以为用者也,汗吐下后,血液之所存几何?而复接结为饮,不能布散诸经,如鱼之失水。能不为之时时动惕耶!且经脉者,所以纲维一身者也,今既失浸润于前,又不能长养于后,必将筋脉干急而挛,或枢折胫纵而不任地,如《内经》所云脉痿、筋痿之证也,故曰久而成痿。
2.10痞利证的证治
伤寒,服汤药,下利不出,心下痞硬,服泻心汤已;复以他药下之,利不止,医以理中与之,利益甚;理中者,理中焦,此利在下焦,赤石脂禹余粮汤主之;复不止者,当利其小便。()
本条辨表里兼证,言“伤寒”以代表证,言“服汤药”以代里证。病为表里,论治法而先言“服汤药”以揭病以里证为主,治当先里。
仲景以治里不当,把辨证的重点引向辨脾胃痞证上,同时暗示辨脾胃痞证有寒热虚实之分,病非是中虚湿热痞证,用泻心汤是达不到治疗目的的。
病若是脾胃虚寒痞证,因其病证表现时有类似实证,对此如果态能抓住证机所在;将虚寒而为实证而用下法,用下之后,势必加
重脾胃虚寒而引起下利证。文中又以假设的形式论述病是下焦虚寒证面用治中焦虚寒证的方法及方药,同样是达不到治疗目的的。病既然是下焦虚寒证,其治应从下焦而治;若是大肠虚寒滑脱下利证,其治当固脱.以赤石脂禹余粮汤。于此仲景又论述病同样是大肠寒下利证,但有滑脱和水气之分、其证机非属滑脱而是水气者,其治则不当固脱,而当利小便,行水气,其用方可参五苓散。
本条从辨表里兼证入手,但辨证的关键不是辨表里兼证,而是辨中焦痞利证及下焦下利证的证机所在。以治法不当为笔法,暗示病证表现错综复杂,但其决定的因素是素体脏腑有否失调及何脏腑有失调,并以此展开辨痞利病证的辨证思路,提示辨证一定做到审证求机,按证机而论治。
《注解伤寒论》:“伤寒,服汤药下后,利不止而心下痞硬者,气虚而客气上逆也,与泻心汤攻之则痞已。医复以他药下之,又虚其里,致利不止也。理中丸,脾胃虚寒下利者,服之愈;此以下焦虚,故与之其利益甚。……此利由下焦不约,与赤石脂禹余粮汤,以涩固泄。下焦主分清浊,下利者,水谷不分也,若服涩剂而利不止,当利小便以分其气。”
温涩固脱止利。
赤石脂禹余粮汤苏石脂碎斤48g大一余核碎,一斤48g上二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分温三服。
方中赤石脂温涩而止利,收涩而固脉络,主肠癖脓血。禹余粮涩肠止泻,收敛止血,固脉络而和大肠。二药相用,善治下焦虚寒滑脱下利证
随证加减用药:若滑脱不禁者,加诃子、鸟梅;若气虚明显者,加黄芪、升麻;若阳虚者,加补骨脂、吴茱萸,等。
《金镜内台方议》:“必与赤石脂之涩为君以固其滑,涩可去脱也。以禹余粮之重镇,固下焦为臣佐使,重可去怯也。以此二味
配合为方者,乃取其固涩以治滑泄也。”
喻嘉言《尚论后篇》:“禹余粮甘平,消痞硬,而镇定其脏腑赤石脂甘温,固阳虚而收其滑脱也。”
本方具有温涩固脱止利作用,主治滑脱泻利证机,可以治疗慢性肠炎、过敏性肠炎、慢性非特异性溃疡性结肠炎等病证而见上述证机者。
2.11痞证预后及转归
太阳病,医发汗,遂发热恶寒,因复下之,心下痞,表里俱虚,阴阳气并竭,无阳则阴独,复加烧针,因胸烦,面色青黄,肤潤者,难治;今色微黄,手足温者,易治。()
本条辨表里兼证。言“医发汗”,以示表证为主复言“因复下之”,以示里证为次。文中特言“因复下之”,以揭病是表里兼证,即使表证已解,法当治里,沿里即使当用下法,也要审证求机,以法选用或寒下或温下或润下,若不加辨证而妄用法,一下不解而反复用下,用下必大伤正气,引起新的病变。对此仲景暗示辨表里兼证虽然正确,但因治疗未能切中病机,同样不能得到治疗目的。以此而论述阴阳俱虚痞证,其病证表现是:“心下痞,表里俱虚,阴阳气并竭,无阳则阴独。”其证机是中焦脾胃阴阳俱虚,清浊之气逆乱而壅滞心下。其治当益阴助阳,和中消痞。
文中通过治表表证仍在,治里里证未除的治疗方法,提示辨表里兼证在某种情况下,疾病的主要矛盾方面可因治疗不当而发生变化,由表证为主转化为以里证为主,因此论治则当重新确立。
辨痞证有寒热虚实,因治疗不当,则会加重病证。本条重点指出,辨虚痞证,病情较重,其预后如何,观察病人的面色至为重要,因面色可以反应病人脏腑之气的盛衰,真脏之气可至于面,故可知其预后也。“面色青黄”其证机是阳虚而不得温煦,寒气充斥而肆虐;面“色微黄”其证机是脾胃生化气血滋荣于面。正如文
中所言:“面色青黄,肤明者,难治;今色微黄,手足温者,易治。”
《注解伤寒论》:“太阳病,因发汗,遂发热恶寒者,外虚阳气,邪复不除也。因复下之,又虚其里,表中虚邪内陷,传于心下为痞。发汗表虚为竭阳,下之里虚为竭阴,表邪罢为无阳,里有痞为阴独。又加烧针,虚不胜火,火气内攻,致胸烦也。伤寒之病,以阳为主,其人面色青,肌肤晌动者,阳气大虚故云难治;若面色微黄,手足温者,即阳气得复,故云易愈。
2.12脾胃阴虚证原文
太阳病。当恶寒,发热,今自汗出,反不恶寒、发热,关上脉细数者,医以吐之过也;一二日吐之者,腹中饥,口不能食;三四日吐之者,不喜糜弱,欲食食,食暮,以医吐之所数也,此为小逆。()
本条辨表里兼证,病以表证为主,治当先表。从仲景言“医以吐之过也”,以示病以表证为主,可因辨证失误,导致治疗失表里之序,可因病者体质而异,可引起或加重里之病证。仲景以此为笔法,把辨证的中心引向辨脾胃阴虚证上。仲景特曰“反不恶寒”者,以揭病由表里兼证已变为单一里证,表证已罢,其治不可再从表证。辨脾胃阴虚证,其病证有轻重之分,轻者“腹中饥,口不能食。”其证机是脾胃阴虚,虚热内生而躁动。其治当益阴和中降逆;重者“不喜糜粥,欲食冷食,朝食暮吐。”其证机是牌胃阴虚,虚热内生,阴不得滋养脾胃,胃气不纳,脾气不运,浊气上逆。其治当滋阴和中,清热降逆。文中又以时间的多寡以及治疗不当等因素为思路,暗示辨脾胃阴虚证,一定要辨其轻重,以法论治。
本条还暗示,辨脾胃阴虚证,尤其是辨胃阴虚重证“朝食暮吐”,应当与脾胃虚寒证“朝食暮吐”者相鉴别,其二者病证表现都比较重,当引起重视。
文中最后指出,辨脾胃阴虚重证因其误用“吐法”所致,其病证虽重,但治疗尚可,故仲景曰“此为小逆”,对此还要根据具体病情因证而灵活辨之。
《伤寒溯源集》:“夫太阳表证,当以汗解,自非邪在胸中,岂用吐?若妄用吐法,必伤胃气,然因吐得汗,有发散之义寓焉,故不恶寒发热也。细则为虚,数则为热,误吐之后,胃气既伤,津液耗亡,虚邪误入阳明,胃脘之阳虚躁,故细数也。”
2.13胃虚寒证与胃实热证的鉴别
病人脉数,数为热,当消谷引食,而反吐者,此以发汗,令阳气微,膈气虚,脉万数也;教为客热,不能消谷,以胃中虚冷,故吐也。(12)
:病人脉数,数为热,当消谷引食,而反吐者,何也?师曰:以发其汗,令阳气微,膈气虚,脉乃数;数为客热,不能消谷,胃中虚冷故也。(第十七3)
本条辨表里兼证,从治法不当而知病以表证为主,治当先表,但因用汗法未能切中证机,导致表邪未能从表解,反而内传而加重里之病证。本文以治法不当为借鉴,进而把辨证的重点放在辨胃虚寒证和胃实热证上。
辨胃虚寒证与胃实热证,文中首先指出辨胃实热证与胃虚寒证的一般表现特征,并暗示在辨证时,除了知常之外,还要抓住证机所在,能够识别特殊表现。文中以举例的形式暗示,脉迟主胃虚寒证,而脉数既可主胃实热证,又主可胃虚寒证,此脉主证机截然不同,如何分清病是胃虚寒证,还是胃实热证?尤其是胃虚寒证脉数,很像热证,这样就要求辨证要知常知变,全面把摆病情,且不可寒热证机不分。
欲分辨寒热证机,细审脉数,有力者为实热,无力者为虚寒。究脉数主虚寒之机,正如仲景所言:“令阳气微,膈气虚,脉乃数也。胸中有心气肺气,阳气膈气,统称为宗气。阳气主固摄血脉,
膈气主行使血脉,阳气虚不得固摄,膈气虚不得行使,脉失阳气所摄,膈气所使而奔波,是以数也。
再者,脉数主热证,热则消谷引食;脉数主寒证,寒则不能食而吐,又是其不同。
《伤寒溯源集》:“若胃脘之阳气盛,则能消谷引食矣,然此数,非胃中之热气盛而数也,乃误汗之后,阳气衰微,膈气空虚,其外越之虚阳所致也,以其非胃脘之真阳,故为客热,其所以不能消谷者,以胃中虚冷,非唯不能消谷,抑且不能容纳也。”
脾胃热证的证治
太阳病,过经十余日,心下温温欲吐,而胸中痛,大便反溏,腹微满,郁郁烦,先此时自极吐下者与调胃承气汤;若不尔者,不可与;但欲呕,胸中痛,微溏者,此非柴胡汤证,以呕,故知极吐下也。()
本条辨证精神有三。一论表里兼证。暗示病以表证为主,时当积极治疗表证,但因未能如此,其表邪未能从外解且乘机传入于里,以加重里之病证。辨里证一定要辨清里之证机所在,针对证机而治之,尤其是病有类似表现,一定要注意鉴别诊断,否则会引起或加重病证。
本条以辨里证未能恰到好处为笔法,进一步论述脾胃热证的一般证候表现。又以治疗不当指出脾胃热证的特殊表现如“心下温温欲吐,而胸中痛,大便反溏,腹微满,郁郁微烦"。其证机是脾胃有热,胃中邪热上逆而郁于胸中,脾中邪热内郁而下迫。究其因,正如钟景所言“先此时自极吐下者”。即脾胃有热,复加治疗不当扰乱脾胃之气所致。辨脾胃热证,其证候表现不管是一般表现,还是特殊表现,只要审明病证是脾胃热证,就可用调胃承气汤。
二论鉴别诊断。因辨脾胃热证“心下温温欲吐,而胸中痛,大便反溏、腹微满、郁郁微烦。”既可见于脾胃热证,又可见于少阳枚证不可用调胃承气汤。
只有仔细辨证,才能辨清病变证机所在。
三论问诊在辨证中的重要作用。文中言“若不尔,不可与”以暗示问患者是否用过何药治疗,对辨证论治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有助于审证求因。
本条辨证主要揭示,其一,辨表里兼证,假如未能及时治疗表证,表邪可乘机传入而加重里证;其二,指出辨脾胃热证,既要辨消其一般证候和特殊表现,还要注意鉴别诊断,方可免于失误;其三,暗示治疗是否妥当有助于诊断,即诊断治疗。
《伤寒六经辨证治法》:“过经十余日,心下温温欲吐,而胸中痛,大便反溏,腹微满,郁郁微烦者,乃属太阳而兼阳明,当审何经而为定治,故有二辨。若已经吐下者,是吐下致伤胃中津液,邪气已陷阳明,而为主治,故当调胃承气而下夺之。若不经吐下,未损津液,而温温欲吐,胸中痛,微溏,腹微满而烦者,邪气仍在太阳,当治其太阳,故曰不尔者,不可与之。见但欲呕,胸中痛,微溏,此乃太阳而兼阳明,莫作柴胡证治。谓非柴胡证,然何以识吐之变?盖因呕,乃吐下伤胃所致,故知邪气不在太阳,陷在阳明矣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